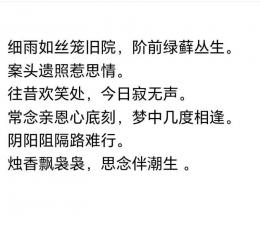“我当时写完老舍这篇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走出来,《花开花落有几回》是我自己在《人有病,天知否》这本书里最喜欢的。老舍就是花开花落,起起伏伏。他升得那么高,又摔得那么惨,最后以死亡告终。很多人都说那天晚上如果他扛过去了,可能就不死了。”学者陈徒手时隔十几年再谈那篇文章,仍然十分动情,对于老舍在那个时代中所遭受的一切唏嘘不已。

青年时期的老舍。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这几年一逢老舍祭日,学者陈徒手都要应付媒体。在北京青年报的大楼里见到他的时候,澎湃新闻记者问他是否厌烦这个话题,是否觉得人们在消费老舍。陈徒手说:“这绝对不是消费,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多次听说,有不少人提议在太平湖设一个碑,写‘老舍遇难处’。我听了心里不好受,但觉得值得做。我觉得老舍的心路历程很值得研究。当时的“极左”政治活生生地就把一个人吞没掉了。这还要下大功夫去反思,还需要跟更多的读者去说、去交代、去剖析。”
老舍的悲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
陈徒手一直在想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是怎么过的:他是怎么离开的家,又是沿着什么样的线路走到太平湖去。那天,老舍究竟在想些什么。那天,老舍可能经过了人艺剧场的门口。毕竟他有那么多部话剧在那里上演,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估计他到那会有个停步,停下来看看那个剧场。”陈徒手说。
和很多人一样,陈徒手对老舍之死充满了兴趣。在三联书店2013年版《人有病,天知否》中,他给每篇文章新增了题记。在《老舍》一文的题记中,他这样写道:“1966年8月他自沉于太平湖,那一天他究竟在想什么?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因何最后在昏暗的湖边身心崩溃?一大批作家学者官员在同样的地方挨打受辱,为什么偏偏是老舍先生‘自绝于人民’?他心里的痛苦纠结在哪里?解不开的思想疙瘩又在哪里? ”
但和很多人不同,他没有选择去还原老舍去世的那一天。《花开花落有几回》直到倒数第三页,才开始讲老舍的的死,从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艺的种种人事变动说起。这段写的很简洁,节奏也很快,像疾风暴雨,一句一读敲打在人的心上。
老舍的死,被揉进了一系列的风云骤变中,是一整个政治变动链条中微小但却不可或缺的一环。“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陈徒手把这一事件浓缩成了这十个字,轻描淡写但又异常沉重。
当被问及这样的写作安排时,陈徒手说老舍之死已经太多人做过了。所以他不想重复,想找些新的角度。作为一个史料收集者,借工作之机看了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机会,使他得以从老舍与人艺的“悲欢离合”中窥得老舍其人,得以把引发老舍死亡的原因往前推,去看看这个种子,在何时埋下。
“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 这是《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的结尾。谈到这个结尾,陈徒手很得意,他说自己写作有个小癖好,就是特别注重每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他喜欢这个结尾,“因为这个结尾给人很多想象。”同时也表明了,老舍的死绝非在太庙挨了红卫兵一顿打那么简单。相反,老舍身上的悲剧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只不过恰好,在那顿挨打后爆发了,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的悲剧因素其实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就埋下了,他就是不被信任。党内很多人对他是有意见的,觉得他是资产阶级分子;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是最根本的。从1950年代初期一直到‘文革’,对老舍的异议一直都在,老舍也能感觉到。”

《龙须沟》剧照,上映日期1952年。
陈徒手说,大家原来总觉得老舍的死,好像是他那天被打之后突然产生的念头。但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和共和国有很多相关联的悲哀”。老舍之子舒乙曾对他说,老舍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光话剧就17部,这是相当高产的。1951年《龙须沟》演完之后,老舍特别高兴,老演员郑榕告诉陈徒手,当时老舍把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他丰富胡同的家中。按照老北京的风俗,请了大厨师,带着徒弟,背着一口大锅,做了一百道菜。老舍在院子里设宴招待。那天老舍喝多了,特兴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陈徒手觉得《龙须沟》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在成功的同时,也有很多悲哀的种子已经被埋下。
“周总理特别喜欢《龙须沟》,觉得这个戏让穷苦人民知道了是谁领导他们翻了身。他觉得老舍的剧本比《人民日报》社论都管用,解决了大问题,让穷苦人民知道了是谁领导他们翻了身。 周恩来跟周扬说,你得好好宣传一下。后来周扬就在《人民日报》写了一大版文章,夸《龙须沟》。还想给老舍颁奖。但马上就遇到障碍,当时解放区来的作家、理论家不干了,说老舍没参加解放斗争,他那时候在美国 。彭真知道以后说《龙须沟》是写北京的,可以由北京市来颁奖,所以后来“人民艺术家”是北京市颁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很多纠结和矛盾。”

老舍喜欢植物。
老舍的力不从心
陈徒手觉得老舍也不是没有反抗,但他的反抗都是一些微小的反抗。舒乙告诉陈徒手, 老舍写《春华秋实》,改了十二遍,光是修改稿就五六十万字。周恩来看了第九稿彩排之后,仍觉得不理想。当时是1955年,“三反五反”已经接近尾声了。周恩来就说,我现在把党的政策完完整整地告诉你,你根据我的结论去写。但是不能太概念化,要艺术。
到了最后,整个剧本,关于大的主题,人物形象等问题,谁都能提意见。工商局代表、资本家代表的意见都必须得采纳。这些老舍都听了,也都改了剧本,但他在最后时刻“反抗”了一下。关于剧名,领导提了一大堆诸如《保卫胜利果实》《在一家私营铁工厂》《为人民服务》等等,多达二十多个,但老舍坚持用《春华秋实》,即使领导觉得这和整个革命斗争的气氛不吻合。
在其余时刻,老舍还是脆弱的,无法反抗的。虽然如此,他仍然努力跟随新中国发展的脚步,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局限性。很多时候,面对革命运动题材,他力不从心。
陈徒手回忆,当时他采访人艺老演员叶子,叶子说大跃进时期老舍腰疼得厉害,实际上他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最多就是在街道动员的时候捐点铁器,因此他和外面热火朝天的生活还是有距离。有时候实在写不下去了,他一幕就写几句话。跟演员说,你们自己去编吧。还有的时候,演员的台词是直接挪用《人民日报》的社论,诸如“共产主义是桥梁”。写《青年突击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根据劳模英雄事迹写。演员们到下面去体验生活,回来直接把素材给老舍,老舍现写。
“所以说他的努力还是有局限性的,他也知道自己干不了这个事情。”陈徒手说,1957年初春时候老舍对自己有反思,他懊恼,觉得自己就是个搬运工,没有任何艺术技巧。“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痛点。他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很成名气的了,写那么好的文字,塑造那么好的人物,再去做这种很低水平的、完全是政治化的工作,对于他的艺术天分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解放后没写什么小说,只有一个《无名高地有了名》。我看那个小说也很生硬。他写字的能力已经彻底被毁掉了。《四世同堂》等作品,这还是他偷偷摸摸写的,虽然也还可以,但是相比他三十年代的作品,确实有很大的落差。后来看他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他已经适应了《人民日报》的语调和情景。一个作家本身独特的个性已经没有了。”陈徒手感叹道。
但老舍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他懊恼于自己写出的文字,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十分积极地进行同类型的创作。他力图让自己的话剧作品反映革命生活,有时候甚至是先于生活一步,呈现出来。
“他写《红大院》、《女店员》都是跟着运动走。《红大院》写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城市人民公社还在酝酿,正在制定方案。老舍抢了先机写,写好之后就开始排练。但城市人民公社迟迟没有成立,戏不好上演。于是全剧组就等待。忽然听说天津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剧组就飞奔去体验生活。但当时经济形势不好,随着1959年、1960年大跃进出现的失败迹象,城市人民公社就一直没成立。所以老舍的剧本赶了个早,可能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了。”



2006年,新太平湖出现在北京,它由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进行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上进行批示。
北京人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样的漩涡也波及了老舍。到了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了。老舍家离人艺很近,走路就能到。以前每年人艺有重要的演出都请老舍去看,到了1965年,人艺不敢请他了。后来他去日本访问,回来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给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发。这对老舍的打击非常大。
同年,《北京日报》还暗地里排了整版文章,批判老舍、焦菊隐。文章都排好了,但可能因为当时领导还没考虑很成熟,就没见报。如果当时按照斗争的程序,一见报,就等于老舍在那时候就作为批判对象,提前被抛出去。但陈徒手觉得,如果1965年老舍就被批斗了,那可能他1966年就不会自杀,因为他就有心里准备了。所以1965年的这次化险为夷,实际上也为他1966年的自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1965年和1966年,老舍的内心绝对是非常不平静的,他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已经非常吃力,还被排斥在外。他积累了好几年的绝望,只是到挨打以后那种绝望突然爆发。虽然说当时有斗争,挨打了,但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极左年代给他的压迫,那种抛弃。我觉得这是他的死因之一。”陈徒手说。
在《花开花落有几回》的最后,陈徒手写了这样两段话:
“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陈徒手说这是人艺的老演员跟他说的。他们说,“文革”之后重新排戏,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复排了这么个戏。他们一遍遍的谢幕,眼泪全掉下来了。老舍不在了,焦菊隐也不在了,都不在了。其中几个演员在“文革”期间也在监狱里好多年,他们都经历了大起大落。重排的时候,演员们台词都没有问题,但他们内心的沉淀都不一样了。
而回忆起1998年在人艺档案室抄档案的那段时间,以及当时和人艺老演员一起回味那个荒诞年代的种种往事,陈徒手也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场梦。

《茶馆》剧照,上映日期1982年。
“档案室在人艺剧场三楼的房间里,都是1950年代的旧柜子。档案保留得特别好,是按照剧组分类的,比如说《茶馆》这个剧组的档案,就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里面有导演的手记、场记图、演员的人物小传。全部都有。
“除了林连昆生病了,于是之老师说话不行了,其他编导、演员我都采访了,特别难得。” 陈徒手至今仍觉得自己幸运。他说作为一个史料工作者,自己大部分时候是在和历史赛跑。跑得慢,就追不上了。而在老舍这件事情上,他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很多单位的档案现在都不容易看到了”。
就像老舍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起起伏伏一样,陈徒手见证了老舍在1950年代之后的起起伏伏。唯一不同的是,老舍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他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无处言说。而陈徒手作为一个史料收集者,幸运地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供人们参考、回味和警醒。
http://www.dxsbao.com/art/12362.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