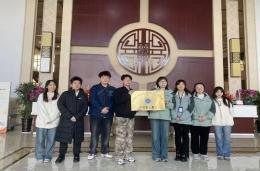我们庄子以衣傍水,正坐在一条名叫刁河的小河南岸。刁河,从长度和宽度上来看,都不能称得上是一条大河,但它的脾气有时候却很差,特别遇上丰水年,雨水过分充足,经常就会泛滥咆哮,淹掉大面积的农田庄稼,幸好有一条长长的河堤隔在中间,我们的庄子才能在这时候幸免于难。
但平时我们对这条河流还是非常仰仗的,吃水用水都还要从刁河里取用。
那时候,村儿里是没有自来水的,全仗着我们家那口古井,村子里的人才能吃的上水,而听我爷爷讲这口古井又全靠着这刁河的水来补给,我们才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我印象里,村子里到了夏天是特别闷热的,而这时候我家的这口大井周围却是能聚上不少人,那是因为这里有一片很大很大的榆树阴。我爷爷也不能讲的清楚这棵榆树到底是什么时候长在这里的,不过这棵榆树像是因为与这古井作伴的缘故,倒是长得十分茂盛,它撑起的大大伞盖能挡出来一片很大的阴凉,给我们这些身处火炉中的人们一份难得清凉。
榆树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身影就是我的爷爷,那时候我爷爷还很清健,他有睡午觉的习惯,但醒的很快,约摸半个钟的功夫,他就会准时蹲在榆阴下边。我爷爷最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事总喜欢拿起锄头、钉耙什么的在树下边捣鼓捣鼓,看看耙头是不是松了、锄面是不是锈了,看得出,他真的很爱惜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他的孩子那样。
下午来人的时候,爷爷总会习惯性拍拍手的灰,站起来问上一句“吃了没呢?”然后转身回屋里提两把椅子出来,接着就是两个人坐下来闲聊家常,慢慢地,太阳西移了,在这当里,有不少人加入了爷爷他们的聊天队伍,榆树下边也慢慢地沸腾起来。当然,只要来人了,爷爷照样是打完招呼就去拎椅子出来,到后来人渐渐多了,已经没了椅子,那些年纪稍微小一点的人就会主动把椅子让给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然后脱了一只凉鞋垫到屁股下边,顺势背靠在树上,那样子,像是比坐在椅子上还舒服些,而爷爷到最后也一定是会把椅子让出去,随手拉过来靠在榆树上的锄头坐到把上去。爷爷的那把锄头把很结实也很光滑,但他每次都能坐的很稳很稳,我从没有看见他掉下来过。
在这一群人中,爷爷和几个年龄大的老友,自然而然形成了人群中的“一派”,他们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讲着方圆几里的大事小事,谁家的人没了、谁家又娶新媳妇了等等等等。我爷爷是毛主席的忠实“粉丝”,虽然毛主席已经去世那么久了,但在我爷爷的心里他永远永远是我们的大救星、活菩萨。有时候,他们可能正在热火朝天的谈论着另外一件事,这时候我爷爷就可能突然来一句“还是人家毛主席能哩很,你看看人家…”接着话题就被他“颠覆性”带偏,而成了关于毛主席的专题故事会,不过,似乎没有人会介意,他们反而像我一样也爱听他讲毛主席的故事,甚至有时候在一旁的妇女们也会静下来听他绘声绘色的讲述,而我的爷爷肚子里好像也装着永远也讲不完、讲不烂的红色故事。
在座的,很有几个和爷爷非常谈的来的老友,有我们的老邻居小爷爷、河堤下住着的王老伯还有南坡的老汤爷,他们这三个老友用“惺惺相惜”来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其中,爷爷最尊敬的要属老汤爷了。
但是后来,老汤爷走了,榆阴下,原本谈天说地的一帮老哥突然少了一个,大家都很难受,气氛也没有原先那么高涨。爷爷心里更是难受,但他依然坐在榆树阴下讲着我们爱听的故事,只不过在这以后,关于他和老汤爷的故事更多了。有一次,在讲到,他和老汤爷1961年在陕西逃荒的故事,爷爷竟情不自禁的呜咽了起来,“那时候,我还不到17岁,饿的两腿就像打了结儿,怎么也站不起来,是老汤饿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把我从陕西背回了河南,我就是到死也忘不了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咱两就是死也得死到一块喽!”…最后爷爷终于没能控制得了自己,抱着头痛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爷爷哭,他哭的那么伤心,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再后来,我爷爷也走了。我记得很清楚,走的那天晚上,是正月初六,爷爷的四肢已经僵硬了,只有眼眶里的那两颗失了色珠子转来转去,来回打旋儿,,我们一大家子都静静地围在他的床头,悲伤之余,面面相觑。我哥哥握住他的手,泣不成声的说:“爷爷,您就放心的走吧,等您去了,我们就把您埋在老汤爷的坟旁,让你们老哥两在地下也能说上话。”爷爷听罢,像是缓了一会,终于闭上眼睛,安心的去了!
如今,两座高坟比肩而立,坟上绿草如荫,一棵榆树耸立坟旁。听,或许,此时此刻,他们又在榆树阴下闲聊了起来。
http://www.dxsbao.com/art/302136.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