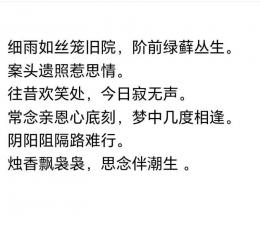这年夏天,整日烈日当空,田里的庄稼怏怏地低垂着头,蒸熟新掰下的玉米,已没有从前那样充盈的汁水,坚硬地像是屋前那近乎皲裂的河床。外婆仰头望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忧愁地诘问着:“什么时候下雨?”回想从前,这时总是雷雨天,下雨时我关上玻璃窗,雨水是像幕布一样铺满窗子,紧贴着下来的。雨后,外婆总爱打开窗子和门,潮湿的风儿迫不及待地涌进来,把我俩的房间洗净,那一刻我如同置身旷野。不过往往这时房门会“砰”的一声关上,像是要把我拉回来——
台风影响到莲花村的一个夏天,我们一家两个人一只狗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大风把外公种的树拦腰折断。我认识我外公的脸,从那张放在供奉桌上的黑白照片,我不认识我外公这个人,我没见过他,在我出生前他就已因病去世,外婆告诉我,家里没那么多钱看病。这时,外婆告诉我们,三爹爹不在了,我很是平静地问道:“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我独自思忖着这件事,恍恍惚惚地提起手边的热水瓶,眼泪渐渐糊了眼睛,一不小心被热水烫了手,像是要把我拉回来。几天后的凌晨两点多,我还没太睡醒,脑子愣愣的。我跪在那儿看着棺材从他家堂屋里抬出来,那哭声好像忽近忽远,我突然想,我外公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吧。我想,我外公现在一定也很伤心。
这就像下雨一样,夏天云从大海上把水带到陆上,下雨,变成水潭,湖泊,江河,长出小草,滋养万物。秋天,再从陆地带回到大海上,到了第二年,它又会飘回来。有人问我:“可是天上的云一会儿变一个模样,而且它飘走已经过了一年,你怎么知道飘回来的那朵云是你见过的那一朵云呢?”我说我就是知道,那是一种直觉。我盯着云看,我想唱歌给它听,但它只会偷偷地飘走,不管我怎么唱都不会停下来。因为云是有云的路的,不是所有的云都会下雨,云总要去他该去的地方吧。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但去和来的中间,总是这样的匆匆!多少个乡村的夏天终究是从我手中悄悄流逝,从我身边飞走了。泡桐树阴下,那个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我再没能回去,一些事物我再没见过。2010年的初夏,红砖青瓦的屋子被推倒,大树在电锯刺痛耳膜的嗡嗡声中一棵棵倒下。一棵年轻的桃树——前一年果树中的生产冠军,在我爷爷的斧头下发出生命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脆裂的呐喊。红砖小路下的泥土地被粗鲁地挖开,一平米一平米拓宽加深,挖出一个数米深坑。我背着书包走到家,我看见的是兵荒马乱的家,和男人们散落一地的香烟。那几年新农村建设改天换地,再没有老房子,石子路,泥土地了,像草原上飘在羊群里流浪的歌,只剩半句旋律;像腐烂在泥土里的树叶,没人注意,没人提起。
后来我也忘了。
读初中之后我几乎半年才回去一次。比我大两个月的狗,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没有了牙齿只能喝粥,渐渐老死了。那只躲着我们偷偷孵蛋的鸡妈妈,曾经在腊月天从雪地里带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被邻居的狗咬死了,几只小鸡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掉进装满水的盆里溺死了。三爹爹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多了皱纹弯了腰,在我离开的那几年,这个最爱喝酒的人,没有一次出现在有我的家庭聚餐上。
原来一切我看来的突如其来都早有预兆,只是我不曾出席。我不能希望静止,更不能希望时间倒流,像云一样,它们都有自己的路,它们总要去他们该去的地方。即使是重新走一遍,云也不会在那一头等我。我只有唱歌给它听,无谓太早或太迟,无谓它的路通向何方。
一阵风吹过,它们沿河而下小成一粒沙子,我咽头腥甜,我实在太累,太累,像犯了心绞痛的卡车,沉重地运走整个下午。我一直走一直走,从一个异乡走到另一个异乡,噢,我也会去我该去的地方,谁能说那里我会不会突如其来地遇见我曾见过的一朵云呢?
http://www.dxsbao.com/art/518539.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