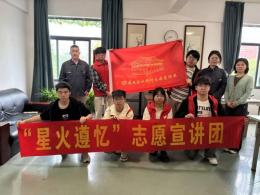溪岸名师讲堂·纪要 | 廖赤阳:留学日本与中日美术界的文化触变——以金原省吾日记及傅抱石书简为中心
2023年11月6日晚,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溪岸名师讲堂”有幸邀请到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廖赤阳教授开讲。廖赤阳教授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后赴日留学,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亚洲文化研究专攻取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华人史、留学生史以及东亚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主要著作有《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络之形成》《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跨越疆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等。本次讲座的题目为“留学日本与中日美术界的文化触变——以金原省吾日记及傅抱石书简为中心”,以线上的方式进行。
傅抱石先生是江西籍著名的美术家,祖籍新余,生长于南昌,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1932年,29岁的傅抱石,在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主任徐悲鸿先生的帮助下,以“考察日本工艺美术,振兴景德镇陶瓷”为主要目的赴日留学,后在1934年4月考入日本帝国美术学校(现武藏野美术大学)研究科,师从金原省吾(1888-1958年)学习画论及东方美术史。
金原先生,于191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21年任日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讲师兼教务主任,1929年参与创建了帝国美术学校,并出任该校的教授兼教务主任,著有《东洋美学》等著作60余部。其代表作有《绘画方面的线的研究》(今古书院,1927年)傅抱石曾撰有《介绍东方画论之权威金原省吾先生》(1934年)一文,并译有金原的《唐宋之绘画》(商务印书馆1935)等著作,在今天仍旧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1935年6月,傅抱石因母亲病危返回南昌,原本计划该年9月再次东渡,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虽然留学时间不满三年,但留日经历对于傅抱石的学术乃至是艺术上的创作都是极为重要的,他不但成功地在东京银座举办了“书画篆刻个展”,更与其师金原省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卢沟桥事变”后,两人的通讯虽然中断,但金原仍妥善保管了傅回国时寄存的作品。金原逝世后,其家属将金原生前的藏书、手稿、书简、收藏品等悉数捐赠给了武藏野美术大学,现在武藏野美术大学收藏的“金原日记”中涉及到傅抱石的天数多达百余处,并藏有傅抱石写给金原的书信二十余封、赠送给金原的印章文物多件以及35年回国时寄存在金原处的绘画作品与图册等众多资料。
这些资料不管是对于了解傅抱石的留日经历及知识来源,还是对于中日近代美术交流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而廖赤阳教授正是武藏野美术大学藏傅抱石资料的主要经手人与整理人。
一、研究前史与问题的射程
二、首先,是关于金原省吾的研究。虽然金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但在日本学界,却很少有人关注到金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大多聚焦在金原对“国语”和“短歌”方面的贡献。廖教授认为,原因可能在于金原在日本美术圈属于官学系统外的在野派,并不被视作美术研究谱系中的正统。甚至在很多学者眼里,金原对于中国美术史的解读还存在不少错误。以金原当时的地位来看,他是无法接触到一些珍贵的中国美术作品原件的,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只能是从出版物的照片去研究,也就不免会出现很多误读。而真正给予金原高度评价的是中国的学者,中国学界不但译介了不少金原的著作,而且研究者们的侧重点也主要在于金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当然,这与傅抱石对于金原的介绍有较大的关系。基于这种研究背景,廖教授提出,从不同地域对金原不同问题的关心出发,可以重新认识到金原研究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傅抱石研究方面,虽然目前已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傅抱石留日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推动。留日体验不仅是傅抱石的个人经历,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众多知识分子的共通经历,对于傅抱石留日问题的探索,能有效帮助我们更好地拓展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但不得不说,相对于留日政治家、文学家的研究,对于留日美术家的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尤其在留学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人和人的互动为中心,所形成的一种知识的循环体系——方面,几乎还是一片空白的状态。
二、问题的开放性与复杂性
傅抱石与金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激荡时代。在这个时代下,东方传统与西方文明、旧学与新学、国民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多民族帝国的疯狂扩张,处处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也处处存在着交汇与融合。在美术也是如此,西方绘画既对东方绘画的传统构成了冲击,也促成了“西洋画”“东洋画”“日本画”“国画”“朝鲜画”等概念的产生。
廖教授借用平野健一郎提出的“文化触变”的理论,诠释了这样一种在历史的非延续性之中编织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的现象——文化在跨境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过滤器的装置,我们一方面选择接受一些外来的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又在抵抗的过程中,重新解释了这些外来的文化要素。在接受与抵抗之间,旧有的平衡被打破,文化系统得以重构,以达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在傅抱石和金原身上,都能看到这种“文化触变”现象的发生。
三、基本史料:金原日记与抱石书简
在武藏野美术大学收藏的诸多傅抱石资料中,最具价值的史料是《金原日记》与《傅抱石书简》。它与公开发表的论文或绘画作品有所不同:论文和绘画是对外的,具有装饰性,而这些资料完全是私密的,是一种最原始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实、详细,具有唯一性的,反映了师生内在人际关系及其心境的私密性记录。
《傅抱石书简》指的是傅抱石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写给金原的二十余封书信。由于中日关系上惨痛的战争历史,当时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对自己的留学体验避开不谈,这与徐志摩等人在谈到剑桥时候的那种神采飞扬是不同的。傅抱石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的论著和演讲中,很少谈到自己的日本留学体验。其与恩师金原的交往,也只有通过后人的回忆可以窥见一二。但幸运的是这些遗留下来的书信,可以为我们了解傅抱石的留学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第一手资料。通过这一史料,我们可以从细节上对傅抱石留学中及归国后的学习、研究、创作、生活、家庭、心境、思想的变化,与金原的师生关系,日本留学对傅抱石的影响等问题,加以复原。
在《傅抱石书简》中,1934-1935年间的书简最多,其中涉及到日常学习、个展筹备、论文发表、著述翻译、访华邀约、采办画材、工作烦恼、家庭状况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通过这些书简,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互动,不仅在于学问方面,还有很多私人领域上的事情,傅抱石都非常坦诚地向老师倾述。他们的书信往来,跨越了战前、战中、战后三个时期,可以见得他们的师生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以下为两人交往的部分记录:
傅抱石对金原的第一印象
傅抱石:“先生性和蔼,当冒昧往東京杉並区井荻三丁目九十番地先生之寄居地时,虽外出,不能自已,以为此果先生之居乎?则木构一椽、备极简陋。…先生极虑专精,校务之外,执笔未遑、室中满地皆书,促做坐其中,挥毫微笑,其沉潜之精神,足使吾辈浅尝者滋愧。”(《唐宋之绘画》第4页)
金原对傅抱石的第一印象
金原:“来了一位叫做傅抱石的中国的省里派遣的留学生……说是想进研究科。虽然不能会话,但是我们的文章可以阅读,也很爱读我的东西,因此来到这里。”(日记1934.3.26)
金原:“在本国说是任过5年江西省第一中学校的高中(高等学校)艺术科主任,有些不可思议。我的第一号弟子,是中国人,真是奇妙的缘分。”(日记1934.3.30)
教学相长
金原:“画论的指导,是对古典一册一册地进行研究与整理,让他读上代中国画论研究等著作。”(日记1934.4.13)
金原:“打算给傅抱石君的《中国绘画理论》作序,读了这本书,没有抱石君自身的见解,而都是古书的摘要,所以我想用此材料并赋予其理论。”(日记1934.10.22)
金原:“[关于《中国上代画论研究》]有一二处我不明白的地方,请教了傅君,也谈了皴法的问题。”(日记1934.5.14)
金原:“对抱石君所提问的《线的研究》中的不明之处又查证了一下。抱石君真是非常细心和严谨地阅读。”(日记1935.1.11)
金原:“《上代画论研究》中发现了不能不订正的地方,因为抱石君和郭沫若提出了两个意见。”(日记1935.1.15)
从深入交往到跨越战火
金原:“今天深入交谈了,也越来越增加亲近之感”。(日记1934.5.22)
金原:“他(傅抱石—引用者注)告诉我:回家的时候,对于占用了老师的时间,感到非常抱歉,但是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非常感谢老师”。(日记1934.6.13)
夜汐:“傅抱石来访,所有预定计划都乱了。不过,即使在此场合,我丈夫也无不快之色,对人非常温情,对此我很感动。”(夫人日记1934.6.19)
抱石:“学生无父,家贫,又无兄弟,家庭负担极重,四五年前,即有志来日本就教先生,但经济毫无,实现不能,去年夏曾走遍中国南北,求大人先生资助,又无结果,后江西省政府以一五〇〇元,资送来月(“月”应为“日”之笔误——-引用者),故当生引为热茶幸事(原文如此——引用者)”(傅抱石书简,1934.8.15(落款))
金原:“今天下决心将堆积的信件写了,抱石君是从六月起就思念不已的。”(日记1936.9.6)
金原:(患感冒)“服用了傅抱石君给我的万金油,已经是九年前的东西了。抱石君现在过得怎样呢?”(日记1944.7.10)
金原:“接到傅抱石君的来信,阅读起来,不禁热泪盈眶”(日记1947.7.4)
四、金原省吾东洋观的膨胀与萎缩
傅抱石回国两年后,中日全面战争正式爆发,师徒二人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金原在此期间,到朝鲜及“满洲”建国大学等地游历讲学,伴随着战争脚步,其东洋观也随之变化。战前,金原的东洋观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东洋是与西洋对置的概念,而西洋,则以罗丹为标准模式;其二,东洋与东洋画的地域范畴,仅限于中国与日本,而将朝鲜排除在外;其三,金原认为,东洋以中国思想和文化为其根源;其四,虽然东洋具有普遍性和共性,但是东洋范畴内的各地域,具有各自的特色和独自性,尤其是日本,具有不同于中国的特色;其五,虽然同属东洋的各地域具有其多样性,但是各地域的独自性之间并无高下与优劣之分。
不过,随着日本帝国的膨胀,金原的东洋观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他的东洋迅速膨脹,其含括的地域,依次扩大到朝鲜→满洲→琉球→南洋,最终与“大东亚共荣圈”相重;其次,在东洋的地域范围膨胀的同时,金原的东洋画的精神核心却在萎缩乃至崩塌,龟缩到日本固有文化与独自传统之中;最后,金原由此陷入了一个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对此,金原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也就是对于日本支配亚洲之矛盾的解決:以日本作为一种纵向的东洋价值体系之中心。以日本之小,来包容亚洲之大。以日本之亲和性来统合“完全不可能混同的二元对立”。
五、日本留学对傅抱石的影响
回到中国的傅抱石,也迈开了自己的脚步。
就像傅抱石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说的那样,从顾恺之开始的魏晋六朝中国美术转换期的研究,以及从石涛开始扩展到明清两代的中国美术成熟期的研究,是傅抱石学术研究的两个主要支柱。这两个时期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转换期,而傅抱石对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正式发端于日本留学时期,是在日本人的刺激下产生,在留学后大成的。
从治学方法来看,归国后的傅抱石的研究,是建立在以实证史学为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既告别了留学前仅停留在史料堆砌的时代,而且也与滕固等擅长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美术的研究方法不同,这显然与金原的指导分不开。
其次,在国画改良方面,留学前的傅抱石是偏向传统派的,他曾在《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中说:“中国绘画,既含有中国的所有形成其独立性,又经过多多少少的研究者,本此而加以洗刷,增大,致数千年不坠。则独立性之重要可谓蔑以复加!……而近代中国的画界,常常互为攻讦,互作批议,这是不知中国的绘画是‘超然’的制作。还有大倡中西绘画结婚的论者,真是笑话!结婚不结婚,现在无从测断。至于订婚,恐在三百年以后。我们不妨说近一点。”(《叶宗镐《傅抱石美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留学后,傅抱石认识到国画改革紧迫性,开始倡议“中国画便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咀嚼古代的残余”,“中国绘画,无论如何是有改进的急迫需要”。(叶宗镐《傅抱石美术文集-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139页。)。并且,在绘画技法、颜料纸张等方面,他也开始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主张中日之间的互学互鉴:
“日本的画家,虽然不作纯中国风的画,而他们的方法材料,则还多是中国的古法子,尤其是渲染,更全是宋人的方法了,这也许是中国的画家们还不十分懂得的,因这方法在我国久已失传。譬如画绢,麻纸,山水上用的青绿颜色,日本的都非常精致,有的中国并无制造。”(叶宗镐《傅抱石美术文集(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再次,在绘画风格方面,留学前的傅抱石热衷于模仿石涛,未能从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形式中脱离出来;留学中,他特别留意在近代西方化的浪潮冲击下,日本画坛是如何积极对应的;留学后,他开始对中国画坛的保守性痛加批判,并积极提倡改革。画风的转变,通过对比傅抱石两次画展(即“东京松坂屋个展”与“壬午重庆画展”),可以看出明显看出。
经过数年的潜心学术研究以及对日本留学经验的沉淀和消化,他的绘画,终于在四川的山水灵气孕育之下,凝聚起“悲家国之颠破,不肯俯仰事人”之坚强的抗战意志,画风为之一变而臻于大成。
其四,日本留学对傅抱石的影响,还体现在对抗意识方面。这一点,不仅限于傅抱石的个人经验,可以视为近代留日学生的一种集体性格。“暂向扶桑赊秀色,后来分作两家春”,清末以来的留日学生,很多都交织着学习和超克日本的个人情怀与时代使命,与此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深受日本文化的洗礼,表现出一种纠结和复杂的日本情结(Complex)。留学期间,针对伊势专一郎《中国山水画史》(1934年),他曾写下批评文《论顾恺之至荆浩之山水画问题》(写于1935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期(秋季特号));针对横山大观的《日本美术的精神》(1939年),他曾写下《从中国美术的精神看抗战必胜》(1940年),在傅抱石看来,“中国的美术,有三种最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全面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叶宗镐《傅抱石美术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就这样,当老师在积极地高歌日本的前进的同时,回到中国的弟子傅抱石正在运用学到的方法深潜于美术史的研究,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融入了日本绘画的手法使绘画风格一新,在抗战中,他的画作中体现了金原的东洋之心,以隐忍、孤高的精神来表现绝不屈服、抗战必胜的信念。他不像当时的抗战画家那样画民众喜闻乐见的黑白版画,也不像徐悲鸿那样以田横五百士和自由不羁的奔马去直接唤醒大众的抗战意志。傅抱石描绘的虽然是四川山水、人物故实、仕女隐士,但他赋予了颓废、退让、闲散、消极、非现实的题材以积极、向前和现实的崭新意涵。他的绘画中,充满了金原在《东洋之心》中说阐述的中国美术的精神――天、老、无、明、中、隐、淡、知、骨、敬、恒。这样,弟子继承了被老师背离和丢弃的精神,在与老师相反的方向上实现了老师教导的那样 “将存在于相反性的东西融汇于一体。”
六、“仙台神话”与“武藏野实话”
讲座的最后,廖教授以“仙台神话”与“武藏野实话”来作总结,生动地阐释了傅抱石与金原的师生故事。大家都知道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但实际上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想象中建构出来的,这一神话之建构有两个支撑点,其一是弃医从文,即国民性的觉醒,其二是战后中日友好的重要资源。而他生前与藤野先生的关系并不密切。但金原和傅抱石的故事却不是“神话”,而是“实话”。通过非公开的、隐私性的《金原日记》和《傅抱石书简》,我们看到的师生关系,它的浓密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了被想象和建构起来的藤野与鲁迅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后的留学潮中,1980年代,傅抱石之女也作为留学生到父亲的母校武藏野美术大学留学,师从于父亲的同学盐出英雄。
这个“武藏野实话”作为一个浪漫的现实,超越了战争与时空,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结束后,主持人郑子路老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青年教师陈艺婕博士参与了讨论,就本次讲座发表了许多专业而精彩的看法。当日,本校师生外,还有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外各大高校的近百位师生出席了本次讲座。
编辑/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新媒体运营中心林熙
http://www.dxsbao.com/news/65647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