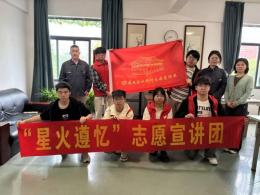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话作本篇读后感的题目:“世有闻耕望之风而起者,予日日引领而望之。”
霜序廿三,初读先生此书,原是带着汲取先生书中养料,化为己有,并一道完成作业的目的而来,最终却陷于先生的风趣幽默的为人、严谨认真的治史态度以及眼光独到的治史方法。
首先还是该明白《治史三书》,何为“三书”?三书由《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三本小书合为其一,前两部都是先生治史之经验,但又有些许不同。第一部将中心放在简明扼要直接讲述治史过程中需要有所注意的部分,第二部的章节多采用疑问形式,从先生自身治史的方向和具体经历给予后进者以更加实际中肯的建议。第三部分看起来相对独立,先生回忆跟随宾四先生进行学习的日子,看似独立,实则前两部分能有所发人深省的观点何尝又没有最后一部分的影响呢。
对我来说先生此书最振聋发聩的部分在于书的第一部分《治史经验谈》,尤有两个观点我看后颇觉得醍醐灌顶。一是“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先生从两个方面阐释这个观点,一个对于除历史外旁的学科知识的博通,一个对于历史本身的博通。人常谓之:“精益求精”“发扬长处”,但没有人能说的上是没有其他短处的。举例来说,把每个人都看做是一个木桶,木桶的边缘看做是这个人所具备的各项能力,他一定有可以说是长处的东西,但相对而言,他也一定有所短缺。对于治史的人来说,我们赋予他的长板以“历史学科”之名,而赋予他的短板以“其他社会学科”之名,长板长了固然不错,但这并非是过独木桥,越长越稳当,同时也是讲求一个触类旁通,你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也不能完全没有。比喻不甚恰当,但总的意思就是,比较在历史学科上造诣近似的人来看,自然是在其他学科上也有所涉猎的人走的更为长远,像是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并不是阻碍,反而算得上是锦上添花。当然,说一个人对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十分了解是不甚可能的,此种说法只是鼓励你在对历史学本身有所掌握的基础之上不要排斥对其他学科的学习甚至可以说是主动的去学习其他知识,作为治史研究的辅助。故对除历史外旁的学科知识的博通是极为有必要的。
再言对于历史学科本身的博通,私以为“一切历史都不能看做是完全的断代史”,不知道先生和老师对我这个观点怎么认为。虽然二十四史其中有多部断代体史书,但我认为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能说是断开的,而属实是连续的,即便是断代体史书,也不能说是一点也不会提到前朝历史。这个观点其实自初中就已经潜移默化地知晓,而今更是根深蒂固,依稀记得彼时的历史试卷中总是出现原因、影响此类题目,而答案也总是出现“为(后朝)奠定XX基础”。同理进行扩展,在探究一个时期的历史时如何能局限于本时期呢,自然总是要“瞻前顾后”的,不仅能避免闹出学术笑话,同时或许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找到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新的角度,从而得到前人不曾得到的新的结论。故对历史学科本身知识的博通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这一部分先生援引钱穆、汤用彤、陈寅恪三位史学大家的事例来论述此观点。“意在钩沉,非必标新立异!”“人人所能看到的书”先生在文中所指的是人人皆可获得的旧史料,而非是新史料。张秋升先生在《关于新、旧史料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中提及新旧史料的关系以及新史料的来源:“史料的积累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史料在不停地变为旧史料。当前,新史料的主要来源大体有三:一是地下出土文献、文物和考古发现;二是虽传世但一直没有被发现者;三是已见史料中隐藏的不被当成史料者。”从新史料来源看,相比较而言最易得的竟然是第一种,而一年中考古发现并不许多,与研究方向一致或能为己所用的更是少之又少,故而新史料十分难得,先生如是说。先生肯定新史料的重要意义,新史料的获得也能推动如今学术界的进一步发展,先生反对的是那些能提前得到新史料却藏着掖着,直到自己“研究出了点什么”才对外公布。先生十足生气,也不过知识说他们自私恶劣,我不似先生般斯文,想换种说法来描述这种人的可恨,可曾见过有一种人手里攥着紧缺的药材,不肯向外出卖,明明能力不足却也想自己研发,以致最后结果造成资源的浪费,延误研发时机,甚至更可恨的是两者皆占。如此这般设身处地可曾能理解先生生气的原因呢,先生或许不止是气,更是遗憾,对所浪费资源的、对所耽误时间的惋惜。不仅如此,先生自当是高度比我要高出许多的,不仅是对一次两次的这种事情不予赞同,更是对学术界出现这种不好风气,以及对新入门学者带来“新史料比旧史料更重要”这种不正思想的气愤。
现代社会“人心不古,物欲横流”,学术界也受其影响,因市场化的环境和官僚化的体制而风气日下,学术腐败和抄袭现象层出不穷。对比先生“纯学术人”的精神,实在有若霄壤云泥,高下立判。在书中先生这样写道,“但就一个纯学术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这段话,足以让那些为名利狗苟蝇营的专家学者为之羞愧。
记得在读此书之前,看过一则书评,写到先生自我解剖般的说自己“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但若做事,则心向法家,奉法有所作为”。这句话令我深有感触,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确实应该有道家清心寡欲的生活态度,儒家珍惜人情的忠恕心理,以及法家严谨奉法的行事作风。知识分子的天职是保持独立的人格,做社会的良心和监督者,不应该为追名逐利,而丧失批判的锋芒。
关于教我们如何进行学习方面先生这样说:“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先生不伐功矜能,不会吹嘘自大说自己这些方法用了就一定能学好诸如此类,它只用最朴素的话语、最实际的经验给我们这些历史学研究的新参者以建议。故而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用心揣摩,才能颇有所获。
最后我想说,先生的文字虽朴实严谨但有一种以情动人的亲切感,读先生所书文字中蕴含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治史者可以将其作为手边读物,常翻常新阅读之后,以便于在学术之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取得更高的成绩。即使是非历史专业的读者,也能从先生不慕名利、踏实为学的精神以及前人学术大家的风范与气度中得到启发,受益匪浅。
http://www.dxsbao.com/shijian/672530.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