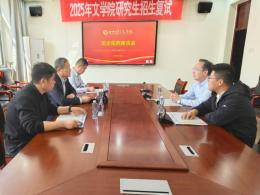石祎阳,男,汉族,2001年出生,山西太原人,智能工程学院通信工程1901班(三达书院)学生。在信院,石祎阳爱上了摄影与视频剪辑,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自己的爱好,看着自己的作品受到大家的赞赏和喜欢,他就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觉得自己的坚持和选择是正确的。
2019年没有疫情,信院也没有封校,刚迈入大学校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好奇。刚开学的时候,每次路过艺术教育中心门口都能看到聚集着很多人,有的是正在举办活动,有的是各个部门、组织在招新,看着那么多有意思的活动,我想:既然来上大学了,那我总得学点东西吧。
有人剪完视频还得改
回到宿舍我就拿出一张纸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列了一个清单,我要去加入宣传部门,我要去学PS,我要去学视频剪辑……
没过几天智能工程学院学生会开始招新,别人还在犹豫去哪个部门的时候,我已经决定去融媒体部门报名了。那时,我压根儿不会想到,就这个决定,让我在大学期间,拍摄和制作视频近200条,拍摄素材1.8万分钟,照片3万余张。现在看到这个成绩,我自己都吃惊不已。

初入视频之门,一个个镜头组合之后的奇妙效果让我痴迷不已,那一段日子,我就跟疯了一般,整个人沉浸在了学习之中,把B站中的各种案例刻在脑子里,然后再自己尝试着用鼠标把它们还原出来。我几乎天天在书院里泡着,不放过任何一个拍摄的机会,然后再急匆匆地跑回办公室,把一段段视频拖到剪辑软件的轨道中,不断尝试着各种组合,不断地研究淡入淡出与各种转场效果。

记得大二那年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在书院活动室进行PPT的完善和视频剪辑,突然窗户外传来一阵吵闹和喧哗,小伙伴们全部跑过去趴在窗户上向外看,只有我一个人不为所动,坐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剪辑。
当时我正在做的工作是剪辑志愿服务队推广普通话的视频。由于前期拍摄时,声音录制效果不好,不是很清晰,不得不做后期配音。这个视频是要给小朋友们看的,如果配音与画面不契合,很可能会对小朋友学习普通话带来不好的影响。所以为了让配音与视频中的口型一致,我只能把声音放到最大,带上耳机一点一点地听,一点一点地去磨合校对。
“快来看,下面有人表白!”一位小伙伴转过身来,热切地招呼我去看热闹。我正专注地盯着口型一点点地拖音轨,完全没有意识到表白是个什么东西。我不耐烦地朝他们摆了摆手,继续敲击键盘拖鼠标。
后来朋友们把他们趴在窗户上看热闹录的视频发给我,我才知道是有人在楼下摆的爱心表白,我开玩笑地脱口而出了一句话“有人相爱,有人夜里看海,有人剪完视频还得改”。我觉得,表白千篇一律,但我的视频必须做到最好。
朋友们由衷地对我表示佩服:就你这个学法,怎么可能学不好?

烈士陵园“悟道”
大二那年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的“三下乡”活动,去了太谷区侯城乡镇马定夫烈士纪念馆。整个队伍里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拍视频和照片,我背着一大包沉甸甸的设备,跟着队伍一起翻山越岭地出发了。
早上六点,我们到了马定夫烈士纪念馆。那边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说很期待我的作品。他们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允许我在整个馆区随便跑、随便拍。
整个馆区包括两座山头,我先去了第一座山的山顶。爬到山顶,我架起相机拍延时摄影,拍完之后立马收拾东西背起设备下山,再到山脚下的纪念馆拍摄文物、资料,完后又背着重重的包爬第二座山。这时,我开始觉得很累了。早晨一开始,我高估了自己的体能,仅仅带了一瓶水就开始爬山了,不想那瓶水在第一座山的路上就喝完了。一直到下午返回时,再也没有水的补充——等到下午三点我们全部结束返程时,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水,我要喝水!”
一路上,我的衣服完全被汗水浸湿,腿在发抖,脚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地方不再敢吃力,感觉应该是起了泡。我咬牙坚持着,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登上了山顶。那里,我看到一些像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队伍正在举行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仪式。我就不顾疲劳,立即装好三角架,调好设备,跟着他们的活动拍起来。
纪念仪式结束之后,这支队伍就开始往下走。我不好凑到人家的队伍里,就一个人抱着一大堆设备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那时,我心里突然有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只有我一个人,不管是去山头还是去烈士陵园,都是我一个人在拍,一个人默默地看着别人在活动。
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回到烈士陵园之后,我在门口驻足了很久,当时想拿上相机冲进去拍,但在这种孤独的情绪中,我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尊重各位烈士,所以我把设备放下,只是走进去默了一个哀。
这种感觉影响了我视频制作的情绪基调。在这段视频中,我用了很多山间的空镜头,来突出表达一种肃穆和永恒的感觉,我觉得,这和烈士纪念馆的基调应该是一致的。

这次经历,让我对宣传工作的理解又更深了一个层次,我觉得,一幅好的作品,应该渗透进自己的感情和理解,有思想的作品才是有深度的。尽管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动的人,平常能躺着绝不坐着,但是这次拍摄以后,为了寻求自己的理解与感受,我经常从这座山头跑到那座山头,用自己的辛苦去换取出色的作品。
妈给我开一下门!
今年上半年刚要开学,结果疫情来了,学校紧急终止了返校。我来得比较早,到学校后一觉醒来学校封了。一部分学生在校内,另一部分学生还未返校,本来熟练掌握拍摄、剪辑的同学就不多,这样一来,我身上的拍摄任务自然就多了起来。基本上就处在团团转的状态——一个活儿还没干完,另一个活儿又来了。
那段时间,从早上起床做核酸开始我就抱着相机拍,拍完之后赶回宿舍上网课。老师刚说下课,我又立马跑出去,跑到工作地点开始拍,抢拍几组镜头后接着再跑回宿舍上网课。大家一般就在晚上9点左右就回宿舍了,我要在办公室呆到11点,有时候甚至可能会拖到1点多。每天晚上我从新媒体中心出来,整个学校的灯已经全部关掉了。

我永远是整个宿舍楼最晚回去的那一个,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在外面敲宿管阿姨的窗户,喊阿姨给我开门。时间长了之后和阿姨也就混熟了,直接喊:“妈妈我回来了,妈给我开一下门!”弄得阿姨看在这一声“妈”的份上也对我没了脾气。再到后来,可能阿姨习惯了我晚归,就给我留门,看到我回来,阿姨就说一句:“你回来了呀,那快把门关了吧,就等你了”。
后来,为了不影响宿舍的人休息,我干脆直接把电脑之类的设备全搬到新媒体中心,几乎住在了办公室。当时新媒体中心的李威老师给了我一个绰号“劳模”。
到五月份,在学校的学生大家都陆陆续续申请离校了,但是我依然留在学校,直到大四的学长们全部毕业以后我才离开,当时整个学校里面只剩下两个学生,我是倒数第二个走的。

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到大四之后其他同学都在忙着考研、忙着考公、忙着找工作,我依旧还是背着相机到处拍摄,依旧还是在电脑前熬夜剪视频。“你不考研吗?天天拍照、剪视频,你图啥?”确实,单看工作量,几乎两三天就要剪一个视频,然后再不停地修改、完善,说实话,在那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下,自己多多少少也有点累和委屈,但看着自己的作品受到大家的赞赏和喜欢,就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觉得自己的坚持和选择是正确的。



我们上大学也不一定就必须考研、必须考公,每个人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我的选择就是信院,就是摄影。如果没有来到信院,我可能也是千千万万考研大军中的一员,可能也正在迷茫毕业之后要去干什么。但是很幸运我是信院学子,它给我提供了我需要的平台,让我感受到了完满教育和书院制大学的魅力。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还会站在六扇门外说一声“信院,我来了!”
http://www.dxsbao.com/xiaonei/555538.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