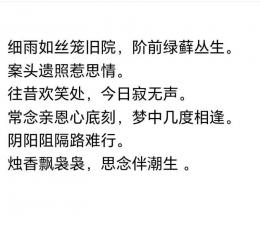“我们这一代也终有一死,我不可能永远做一个幸存者,死亡的筛齿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
半秃着的头、黝黑粗糙的皮肤、眼角爬满了细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还有些泛黄——他,叫袁凌,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陕西农村,是一位资深记者和非虚构写作作家。
出生农村的他,从小就对生命的脆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把命运比作一幅巨大的筛篮,只有躲过了筛眼,留在筛篮里的人,才能够存活。他曾感叹:“一个乡下孩子活下来和长大的过程,也就是他身边的人不断死去的过程。”因此在成长过程当中,他见证了实在太多的逝去,而这些逝去,最后都存留在了他的故事里。
时隔多年,他依旧清楚地记得。2001年,当时的袁凌刚成为《重庆晚报》的一名调查记者。那一天,重庆的烈日似乎是想要连空气都融化,一路上人迹难寻。袁凌穿梭在重庆两路口河菜园坝火车站之间的棚户区,寻找着这个女孩。初次见到她,是在一辆板车上。女孩坐在车上,肚子肿得很大,双腿也随之浮肿,已然丧失了行动的能力。养父母从早到晚在外讨生活,女孩无人照料,大小便都只能在车上解决,接近40度的大气中混合着灰尘,夹杂着恶臭。
在这之前,女孩被送到附近的一所妇幼保健站进行检查。结果显示,女孩的子宫已经完全被摧残掉,而且女孩的先天性心脏病还因此诱发。
他蹲下身,想要从女孩儿口中问出一些以前的事情,可女孩只是盯着他,默不作声,甚至夹带着一丝敌意。所有的担忧汇聚成一阵冲动,袁凌接着问:“你想不想活?如果想活,把真相说出来,才会有人帮你,不然就没人能帮到你了。”最终,袁凌得知了真相。于是他当即回到报社,写下一篇名为《谁来搭救小红萍》的报道,随即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可正当袁凌想要再为女孩做些什么的时候,也就在报道发布的第二天,他收到了小女孩逝世的噩耗。最后,袁凌只是在书中写道:“我没能帮到她,尽管她曾经面对着我的眼睛,留下遗言:‘我想活’。”
但是袁凌本该活在聚光灯下。
当年,他是当地唯一走出大山的大学生;后来,他考取了复旦大学研究生;在2003年,又考取了清华大学博士——一切本都足以让袁凌过上舒适的生活。
然而,他却不止一次地选择了清苦。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乡村才是自己应该待的地方,不管是为了文学创作,还是为了新闻信仰。他只是本能地选择了用笔墨给予底层人民更多的关注。回到家乡之后,袁凌沉浸写作,并且乐在其中。
他时常与当地的一些“阴阳先生”交流作伴,因此见识到了常人见识不到的生死之事。或许也正因如此,袁凌对死亡才有了如今这样透彻的见解,也才会在对生命的敬仰上达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可是,他的耳边也会时不时传来质疑:当地的人们只是以为,他回到家乡是迫于漂泊生活的难以维持——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信仰,他的狂热。在被迫离开家乡的时候,袁凌承认,自己曾经一度掉入了文学的深渊之中,并且无法自拔。但他也确实后悔:“可是,这是一种罪,我当时就是把自己填进了我的深渊,还填进了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最后还失败了,我最终没能一直待在那里,出来了。”
回到城市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他投稿处处碰壁、在多家媒体辗转但一直无法安定下来,成为了曾经同事的属下、拿着大学毕业生的薪水、睡着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出租屋。死亡不断叠加,生活不尽人意。而这一切对于袁凌来讲,无疑都是沉重的打击。因此,对于袁凌来说,那段时期是灰暗的。
好友柴静曾说:“他不允许自己转过头去,就好像他活着对死者是个亏欠,些微的幸福对于这些苦难之人是个亏欠。他的写作,是浸没在这些人的命运里,活上一遭,以作偿还。”
但所幸,袁凌没有崩溃。他曾说过,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忍心的过程,这就是他对整个生命的感受,就像他见识了那么多的死亡,经历过锥心的情感挣扎,可是没有办法,还是要硬着心肠活下去。
http://www.dxsbao.com/art/156667.html 点此复制本页地址